
01
办公室的窗前,有一株水杉,今年端午后搬过来到如今,我看着它历经了一个四季的流转,从新枝初发,到春意盎然,从凄然枯暗,到叶落条黄,从盈盈蓬蓬,再到影只形单。
有时侯斜倚了喝酒吸烟,碰巧会想起一些同学,非常是这些早已许久没见的老同学。
02
那时侯刚才搬到庐江城区里来,我在一家单位做着跑腿的差事,虽然成天被人呼来唤去的,倒也没感觉委屈。
年青人嘛,你不跑腿,谁跑腿啊。
由于上街的机会多了,我的一个收获就是,很快摸透了那几家藏在里巷里的小书城。
扬州饭店斜旁边的文汇书城,好多人肯定还有印象吧。老总叫李华,是个戴墨镜的不白的年青人,听说是老师,看起来也像。
文汇书城不仅教辅材料,一个特色就是文艺类书籍了,我的世界名著们,大多都是这些年从他家买的。
虽然背后也据说李老总很精明,而且我却没有觉得到。
他总是很客气,也会跟你聊一些诗人的往事,出版的续作,这对我们那一拨文学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
有时侯想买哪些书,店里没有,他很诚恳地请我们登记出来,过不了几天,店里的女孩们都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买了。
有时侯没带钱,或则不够,也没关系的,书可以取走,上次再给钱。
有一回,劈头遇到一套卡夫卡的全集,看我嫌贵吃惊了,李老总主动招呼说,真喜欢啊?好啊,好书也要遇对人呢,我给你打折吧。九折,贵么?七折?那叔叔半买半送啦,八折八!钱不够?下回补呗。
我欢天喜地抱着一大摞白色的精装版卡夫卡走了下来,心中饱含了对他的感激。
后来想,或许是生意经呢,而且我还是更乐意,当成是同学间的一种理解与呼应。
那时侯我最期盼的,就是替主任到会招开会,匆忙去点个卯,掉头下来栽进文汇书城里,听到差不多要散会了,再回来露个脸蛋。
遇见大会纪律严的,我就下来借一本薄薄的小诗选,半天会开出来,小书也就翻完了。
那时侯我很奇怪,为何开会总是要念这么长的报告,是怕下边的人认不认字,还是怕她们回家不肯看,没有道理嘛。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些开法,让我看了不少闲书呢。
其实更要谢谢李老总的热情和包容,容许我自如地进出文汇,随便地借还新书。
在街上遇见雨天了,我会尽可能地赶赴书城里去避雨,熟悉的笑吟吟的店员们不催不撵的,任由我看见雨停了天晚了,还赖着不走。
有一年冬天下大雨,我的一位绘画的同学问我,那里的景色好看啊?我带他去了文汇书城旁边。
巷道寂静,雪花飞舞,柜台里坐着店员小朱女孩,端庄水灵,穿一件崭新的粉紫色短裤,在翻看一本新书。
文汇书城开了好些年,突然就关了,听说李老总是去北京发展了。
我仍然希望他的事业做得更好,如同问候一位老同学。

配图:沈萍
03
扬州城区如同一盏灯,我们这种农村的儿子,憧憬它充溢下来的诱人光晕。知道它的烫人与炽热,那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如同一只只卑贱的蟑螂,干劲竭力展翅扑腾,早年在乡下的同学们,陆相继续地经由各类路径,来城里安了家歇住了脚。
我的非常好的一位哥们陆树茂,当时在城郊桥南借住了单位一间破旧的小库房,和丈夫过起了贫穷,而且温暖的小日子。
我那时侯是光棍,有的是空闲,她们就常常喊我过去喝水。我晓得她们的手头显然是很不充裕的,即使是添双牙签的事,而且次数多了,也还是个负担啊。
之所以老是请我过去,一来他猜想我由于工作的缘故,精神不是很激奋,人也是疲沓的,他希望我振作上去。二来可能她们也是认为日子过分冷清单调了吧,有个伙伴来打圆场,少些人间喧嚣,总是好的吧。
我记得好多次,在她们的小屋里喝水闲话的情形。
有一回下雪,我们哥俩就坐在门槛里,正对着院子的天井。
雨大呢,一幅珠帘从天而降,院东角的斜眼柳树,不断地折下树叶,掉在地上,马上又被冲毁,竖着几根,横着几根,堆起一汪积水,亮霍霍的反着光。
姐姐在前面忙着给我们再添一个葱头炒猪肉,一个茴香蛋花汤,还问我们,要不要再去买一点盐水玉米米。我说够啦,不要的。
陆树茂大手一挥,你不要打搅我们谈诗撒。
他趁着酒劲站上去,手里拿着牙签,敲了盛玉米米的空盘子打拍子,饱含激情地诵读了李白苏东坡李商隐的诗。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我到如今还记得,他背完这一句,旋即粗重地敲打盘子的声音,就像沙场秋点兵。
姐姐捏着一把芥菜直冲过来,连声问如何了?大婶哎,你瞎兴奋哪些?
我的哥们她的儿子陆树茂先生,很洒脱地把一双牙签,扔到大纸箱拼上去的椅子上,意气风发地拍拍我的膝盖:兄弟,我们喝水!
我还记得有过好多个春天的夜晚,我们就坐在他的院子子里,畅谈人生理想,痛骂单位官僚。
月亮如银盘,自东而西,一点一点地偏斜。
院子子如同是打着灯光的舞台,澄澈的焦段,如同是被风吹动的;
地上一团一团的影子,犹如一只又一只,呆头呆脑的寄居蟹。
漂亮贤慧的姐姐,坐在他身旁的小板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他撵飞过来的蚊子,最后撑不住了,掩了嘴,打个哈欠说,大家哥俩聊吧,我告辞啦。
后来这一对良人辗转去了邻县东台,又去了南京,我早已甚少再看到她们了。

04
我如今还是不能确定,小解艳究竟算不算是我的同事。
由于她仍然随自己高兴,有时喊我哥哥,有时喊我弟弟。
她认识我的时侯才7岁吧,她的母亲是我们中学的面点师长,对我们这种初次离家住校生活的年青人非常照料。
休假的时侯,我们有时不回家,穿了一件大红呢夹克的小解艳,做完作业喜欢撵着我们玩耍,我们会哄她去饭堂旁边的小木排上,蹲着给我们洗碗筷。她是个活泼懂事的儿子,也非常聪明,好看。
后来我们离开了中学,就不再有联系了。
有一年返校,突然听到她在南边寝室的空地上,夹在一排女孩中间练习跳健美操,长发齐齐地甩过来甩过去的,听到我们了,脸瞬间涨得通红,故意不看我们了。
她长大了,念高中了,是个胆怯的小女孩啦。
再后来有一次,我碰巧据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的邮政大学了,很为她高兴,就兴冲冲写了一张贺卡寄给她,竟然收到了她的回信。
时常我会和她通一次电话,听她聊聊高兴的失望的事情,还有说她恋爱了,男宝宝对她挺好,关键是很帅很优秀。
汪曾祺先生的选集出版了,我看见报纸上的介绍,非常想买,刚好这天她打电话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买一套。
电话那头的她很高兴地说ok,非非思呀。如同我交代给她多么光荣的任务。
没几天,沉甸甸的一套书到了,我要给她书钱,她很不高兴,隔著电话我都能想像得出,她撅着嘴吵架的模样。
中学生那里有钱啊,我执意寄给她了。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后来的一次,是夏季,她突然出现在我的单位旁边,还送了个小螺号给我。她告诉我今年暑期后就结业了。
我有一次和她说起过,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可以,从螺号里,听到遥远的海风的声音。
她刚好和朋友去了上海海滩,顺便给我买了一个。
再后来她结业了,回到市区下班了,也没和我联系,我还是在一次大会上意外地遇到她的。
我记得请她和男同学,吃过一次会招的酱汁螃蟹,还出席了她们的婚宴。只是认为很抱歉的是,后来她的单位动不动就分派指标任务,我的能力很有限,帮不上她哪些忙,也就不太好意思去看她们了。
好在据说她们很快调去南京或则北京的公司了,日子也过得很幸福吧,真的替她们高兴,也为她们骄傲的。
两个年青人凭借自己的能够,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就早已充分证明了,她们是很优秀的。

05
这种天里,窗外的水杉,在几场小雪之后,透出更浓厚的青绿。
我晓得它很快就要迎来,它一年中最丰茂的岁月。
但是,在那之后,它也会难以防止地进入它的萎靡。
我就想,或许我们就是一棵树呢,因缘际会遇到的一些人,有的就像是一阵风,刮过来,又刮过去了,无端地消失了影踪。
而有些,却似乎是一片片新叶,长在你的树枝上了,而且还是禁不住岁月变迁,日升月落,总算还是离你而去了;
来年又生出的碧绿,虽然早已不是那一枚叶子了。
然而,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念起,当初的那一片暖意吧。
同学啊同学,在这些繁忙的街头,或则是慵懒的午后,是不是有一些顿时,你可曾想起了我?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信息真伪需自行辨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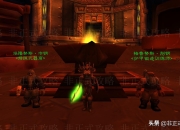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