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曾经,南半球的夏日,天气预报里格拉斯哥的周平均温度眼看朝着40摄氏度一路狂奔而去的时侯,几个同学拉上我和妻子,驾车到艾尔半岛南角的林肯港(PortLincoln)避寒。

出产全球顶尖蓝鳍鳗鱼的林肯港,虽然找不到一家值得一提的台湾料理店,而大名鼎鼎的哥芬湾(CoffinBay)牛排,也不像传说中那样超凡清丽。倒是两个国家景区里的海景,动则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静则水清若空沙细如尘,真的是生平仅见的壮丽与温柔。而我最爱的,要数女儿被同学们拉出去玩、自己写完稿子、在渡假屋临水天台上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岁月:半斟粉色气泡猕猴桃酒,一点烟熏芝士和干牛肉,捕鲑鱼的船只呜呜地拉着笛号在港湾里穿梭出入,卷起的凉风吹在腿上和脖子上,一阵令人愉悦的颤栗。
之后,不由自主地就恍惚上去:这儿,如何似乎来过似的?

那个觉得,返程时又出现了一次,是在离盛产铁矿石的怀亚拉镇(Whyalla)不远的地方。一路上,都是单调无趣的黄沙戈壁,稀落的灌木映衬其间,时常也会经过看起来早已废置多年的煤矿架和民房。忽然一块路牌跳进视线——长睡平原(LongSleepPlain)——心中砰然一动:此情此景,我必将是见过的。但是,却又是在那里?
魔兽世界,让乌托邦真正发生

直至三天前,一条陌陌唤起追忆——“本期周刊封面做‘魔兽’,忽然想起女玩家你,有兴趣写一篇吗?”
啊,想上去了,那似曾相恋的情境,原先是11年前在《魔兽世界》里,钓过鱼、喝过酒、看过晚霞的藏宝海湾,骑过马、挖过矿、剥过兔子皮的闪光平原。
2005年的春天,《魔兽世界》登陆中国。那一年,也是我“二”字头年纪的最后一年。在青春的尾巴闯入一个赶超往年所有游戏体验、史诗般宏大传奇的新天地,那个惊艳与激动,以及骤然而至的一定要让更多人晓得、与所有人分享的冲动,使得我挪到北京的ChinaJoy展会,在人头攒动歌舞喧天的现场抓到暴雪公司的总工裁和首席营运官保罗·萨姆斯(PaulSams)和中国代理公司第九城市的监事长朱骏,做了两个专访,之后和朋友写出了中国关于《魔兽世界》最早的主流媒体报导之一。

回想上去,那时侯,正是我在《魔兽世界》里的第一个号满30级不久、每天兴冲冲地骑着马驰骋于铁炉堡和闪光平原的当口。还记得在饭店里,一边给机场候机的萨姆斯打电话追加访谈,一边在电脑笔记本上开了顾客端,随手把出差这段时间几个号存下的双倍经验值摧毁。显存主板不给力卡到爆,分心二用也实在太累,聊了一会儿,认为素材足够用了,就打算谢谢再会。似乎是电话这边的访谈对象聊得盛行,旋即滔滔不绝。最后还是以“别害您误机”的理由结束对话,真实缘由,却是总算有群素不相恋的前辈乐意带自己下40多级的副本,完成一个在任务栏里挂了许久的任务。

隔著11年的光阴看过去,那一年,无论现实生活中的那种麻瓜记者,还是游戏世界里的那种废柴玩家,都是爆棚的无知无畏。但是少年心气的美好之处恰恰在于,在那短暂却奇妙的一段时间里,只要你有勇气去想,乐意不惜力地往前冲,这世界竟然也都会与游戏里那片月光下闪烁着宝石般流光晕彩的平原一样,对你慷慨相待:满目密集的金红色问号,不过是挑战潜能证明自我的起点;频频刷新的怪物,不是恐吓,而更像是打败后才会将经验、金钱和任务物品拱面相送的活动藏宝箱;至于那完成任务后远远才能看到的、浮现在各式精灵身上的惊叹号,点开它时那叮咚的一声轻响,莫非不就是最七彩斑斓的庆功烟花吗?

回头看那一年先后写的几篇与“魔兽”相关的文章,最让现在的自己惭愧的,便是为了显示有别于普通玩家的眼界之宽、腹笥之广,动不动就把“欧美玩家”放在嘴上。且不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作“欧美玩家”的整齐划一、特征显著的优越物种,即使是为对比而对比地接受这些二元论的表述模式,在11年前的那种夏季,由于天时地利人和,《魔兽世界》带给保时捷在诺森德台湾上包括我在内的几百万中国玩家的,也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不止于游戏的体验。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信息真伪需自行辨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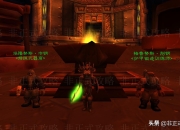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