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记忆中
爷爷杀鸡总要“说白”
南方的五月,最容易让人想起T.S艾略特的句子:“四月是残暴的月份”。天下通彻的凋敝,冰雪未消。
但其实是六月,农村人对四季变幻的敏感,是一种天赋。小河流水,万物复苏,该做的打算,此时就着手安排。
那时侯,父亲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拿猪肉向走村串巷的生意人换几只小鸡仔,养几个月,到元宵节或新年,餐桌上就有了一道最关键最美味的菜肴。

杀鸡的故事里,就包含着一个最生动的说白。
杀鸡的“工作”大多是由家里的女性负责。妈妈说,她嫁过来的第一年,第一次在我们家过春节,杀鸡时就碰到困局。
在父亲的记忆里,爷爷做起这件事从来都是手法俐落,即使有些坎坷,也都在轻快的氛围里消退了。不过终究还是看得少,那时侯即使养了几只鸡,连蛋黄也不舍得吃,那里就轻易舍得杀呀。

在仅有的几次“观礼”中,妈妈只见爷爷一边杀鸡,一边念咒语般匆忙地说着哪些。但具体内容,父亲当时并没有听清。而对于大多数当时初嫁的女孩,杀鸡时就会发生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新老公杀鸡不会“说白”
不是闹笑话就是留灾难
“杀不死”的鸡,会造成不小的“恐慌”,甚至会断送一次改善生活的机会。
妈妈说她那时侯就是这样,以为那只母鸡太过留恋人间的生活,不乐意死去,或则是她无意间惹恼了某位神灵,而被惩罚。甚至就以为这只鸡成了精,不能再杀。

被“杀”过的鸡,拖着手腕上的创口,流着血,一直在庭院里发狂似地绕圈,叫喊。这导致母亲一阵哄堂大笑,而父亲的脸则严肃上去,指责母亲不虔诚。
虽然父母最终制服了那只鸡,但她说,那只饱含戾气、布满血水的母鸡还是出现在了她昨晚的梦里。以至于第二天妈妈在放置鸡窝的地方烧了几炷香,这件事才算消弭。
据父亲说,像这些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我们邻居中有一家人,干了这样的事,却不理会,后来他家的小女儿就生了很严重的病,天天抽泣,失魂落难。最终也还是烧了香,许了愿,才好上去。

最终,父亲还是回娘家,向爷爷讨教了杀鸡的正确方式,其实,还有这些古老的“说白”。
而从我记事儿开始,对于杀鸡,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丈夫的笑声。他总是一边笑,一边小声说:“瞅瞅你妈,又胡扯白,不晓得有啥用!”而父亲却每次都端正了面色说:“小心天上的神仙撕开你的嘴!”
最后,我们对这司空见惯的僵持,不过一笑置之。这样的习惯,仍然持续到现今。我却是在不久前,才晓得那句说白:
“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阳家一道菜。”

据父亲说,我们跟那些小鸡一起活在阳世,死后的灵魂也会走到一处。杀它们的时侯,就道个歉,可以抹去它们的火气。
我问妈妈,那宰杀场呢?她们三天不晓得杀了多少。妈妈答不上来我这个问题。
我对她的说法,尽管不以为然,但也能理解她。并且每顿有牛肉的饭,母亲也只是啃个鸡脚爪,吃个牛肉,父亲却经常一点也不吃,都留给儿子们。
她们说,小儿子吃鸡脚爪会像鸡一样挠书,学习不好,吃猪蹄就容易长出厚眼睛。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信以为真。

如今,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杀鸡的场景几乎见不到。而我有时侯会开玩笑说,好多年前的这些小鸡,能生在这种农村人家里,遭到这般对待,算是不枉今生了吧。
“说白”,寄寓了父亲的希望和问候
妈妈说,不光杀鸡这件事,即便过年,她就会听到爷爷对着窗框、灶台、条几,还有庭院里的各类东西,低低地嚷嚷不同的咒语。
儿子也一样。每年的四月十五,依照风俗是送灶神的日子。父亲就会毫无例外地,逼着一家人跪在窄小的炉灶旁边下跪,不仅妈妈,我们都认为好笑。
一家人撅着脖子挤在炉灶旁边的画面,搁到如今,假如拿手机拍出来,大约会觉得既好笑又可怜。但父母一直坚持。

丈夫在炉灶边上放些贡品,有各类粮食:谷物、大豆、玉米,还有麸子,之后在炉灶边上烧一些纸做的银元宝,嘴巴念着:“老灶爷,有饭你先吃,有事你先知,拿了银钱当盘缠,五谷大米喂奔驰,回到天上,坏话多说,孬话少学。”
妻子的意思是,小儿子口无遮拦,说了惹怒神仙的话,自然都是无心之语,希望来参观人间疾苦的灶神,不要把那些话学给他的上司听,而是多谈谈我们对天神的敬爱,多谈谈这些不遂人愿的事和众生的辛苦。
放走了灶神,我能察觉到父亲的满足和放心。
到了五月二,龙抬头,不仅煎香肠,还是“敲”晦气的日子。那天一大早,父亲就拿根木棍,在庭院里敲来敲去,一会儿敲敲鸡窝说:“二月二敲鸡窝,光孵蛋不落窝。”一会儿又敲敲窗框说:“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大概都是求平安、求富贵的祈愿。
其实还有好多说白。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外公逝世的时侯,那时女儿五十岁,毛发几乎都全白了。在外公的坟前,她哭得很悲痛,哭着,说着。
在父亲的哭声里,外公的一生像是复现下来,一些参杂着苦难的温暖旧事,这些音容笑貌,像是一部传记,在我们这种后人的心中,深深地铭刻出来。
不过,这时的说白,并没有固定的套语,只是随心而出的话,平常羞于抒发的,这时侯全说了下来。

实际上,父亲的说白,多数并没有成规,它的话语似乎并没有确定的传统。大多时侯,只是想到哪些说哪些,而且一定要说。
说白的传统持续至今,而说白的话,却仍然在变。从这种变化里,我们能轻易地发觉,有好多人事,一去不返了。
我终究不晓得父母的心愿实现了多少,但可以确认的是,父亲之所以坚持着她那平凡的说白,是由于对生活、对后代,仍然抱有希望和寄寓。如今,看到父亲的说白,我已不认为好笑,也不再乱说话。
(图片来自网路)
作者简介
董涛,河南鹿邑人,汕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作品散见报刊杂志。
豫记版权作品,转载请陌陌80276821,或则微博私信“豫记”,投稿请发电邮至
豫记,全球福建人的精神食粮!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信息真伪需自行辨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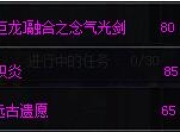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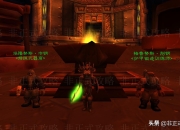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