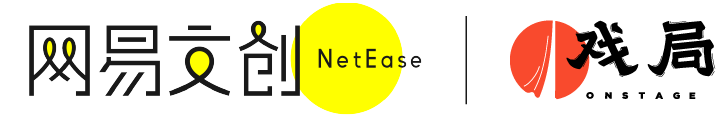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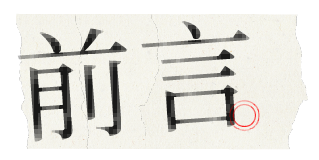
回婆家出现以后,惟一还完全未知的就只剩下徐凡的那本红皮电脑了。那儿面,会有她父亲的死亡真相吗?
如今,我们就将电脑里的内容,公开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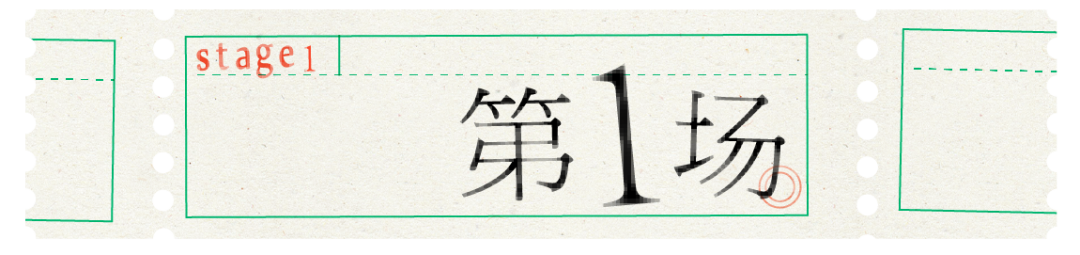
阿几始终认为自己生错了性别,她恨自己是个男孩。
自从她记事起,阿爸对她就没摆过好面色。逢年过年更是一场恶梦,同事们免不了指着阿妈评头论足。阿几从来没见过阿爸维护,反倒有时都会附和着爷爷奶奶说教阿妈。
阿妈脾气软,脖颈子更软,说话办事没个自己的主意。为了求个女宝,他人说哪些都信,哪些秘方怪方都敢尝试,哪怕损伤自己的身体也在所不惜。
谁家添了男丁,在村庄里是值得敲锣打鼓、大摆宴席的喜事。阿几六岁那年,父亲出生了。她就坐在角落里,听着爆竹声传遍大道小巷,头一次听到阿爸身上有了微笑。
那是释怀的笑,宣告自己总算卸下了传宗接代的重任。
正如阿几担忧的那样,自打儿子出生,阿妈的身体就垮了。月子里如何也调理不好,头晕耳鸣成了家常便饭。家里随之少了干活的主力,养家糊口的重担刹那间落在年幼的阿几头上。她晚上学着锄草苗、栽桃树,夜晚补学堂里落下的功课。阿几想,只要自己显得更优秀,阿爸阿妈都会像宠爱女儿一样,分给自己多一些关爱。
这个念头是从哪些开始破灭的呢?
大约是她从桃树上重重地跌出来,手指手臂紫了一片,回到家却看着一家三口享受着天伦之乐,自己却仍要被阿爸指责毁了苗木的时侯;亦或则是她责怪荞麦饭不解饱,想讨一碗父亲手里的肉汤,却正好对上阿爸揶揄目光的时侯。
起码阿爸还乐意供她读书。阿几从不责怪哪些,只是多了些对英语课本里这些美好画面的向往,阿爸阿妈的疼爱,只存在于她幻想中的清寂之地。
但是往旧事与愿违,在阿几十二岁那年,父亲遭到事故意外逝世。阿爸突发肾脏病,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身体大不如前。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阿妈两只耳朵都快要哭瞎了,愁得一夜白了头。
阿几在旷野坐了一下午,决定舍弃上学,专心照看果园。她剪短了碍眼的麻花辫,换上男宝宝常穿的条纹衫,这样也许会让母亲心中好过一点。

每到夜晚时分,阿几都会乘着月色偷偷溜进学堂里。似乎已经退学,她却始终对读书有着莫名的执念。她翻窗进了寝室,眼神朝到处张望,最终落在一张整洁的书房上。
书本根据规格大小整齐列举在抽屉里,桌面一角摆放了本红皮字典,封套右下角被磨掉了皮,白纸早已微微泛黄。阿几用手抚弄着,想起自己遇见认字的时侯也会认真去查。共有的小习惯让她顿时对书的主人形成了一丝好奇。
阿几从书房里抽走两本书带回了家,书本每一页都认真记录了当堂笔记,字迹苍劲,书面也十分干净整洁。她一边翻一边想,这一定是个心思质朴的女孩。
转天太阳还未升起,阿几又把书送回了寝室。
以后每天都是这样,阿几下午回家温习功课,趁天亮再翻墙把书送回去。她做得很慎重,还书的时侯会根据记忆里的次序摆放好,防止让人发觉异常。
过了大约一个月,月色刚爬上树梢,阿几又如往常通常翻墙躲进学堂。奇怪的是,明天她总感觉有东西窸窣翻飞。
阿几把手伸向书房抽屉时,忽然被一股强力摁在地上,脖子被紧紧掐住。她仰头,对上一双闪亮如星河的耳朵,只是此时少年的眼瞳里满含提防与戒备。
“你是谁?为何要偷我的东西?”
被捉个正着,阿几瞬间慌了,眼睛动了动想解释,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最后支嗫嚅吾地憋下来一句话:“我,我只是想瞧瞧你的书。”
谁料少年看到这话也愣了一下:“你,你是女孩?”
阿几面露惊讶地点了点头。
她被扶了上去,与此同时她震惊发觉,少年竟拄着一副手杖。
“不好意思,刚刚把你看成了女孩,所以才……”
少年的话没继续说下去,阿几早已愧疚地垂下了头。她不晓得该说点哪些才好。明明是自己的错,这人还抢着歉意是哪些道理?
还在思索的时侯,少年早已从抽屉抽出了几本书,递到她面前:“我的书可以借你随意看,之后你就不要翻阳台了,这样太危险了。”
阿几神色错愕地举起头,看到少年冲她笑了笑。

一来二去地,两人就这样熟识了上去。少年会在晚上下班后给阿几温习功课,阿几则会给他带些自己做的饭菜。
家里的大黄狗对所有陌生人都参杂着敌意,惟独对少年没有。少年蹲下体亲吻大黄时,它会乖巧地用鼻子贴上他的手臂,亦或是舔舔他的手背。
少年似乎是邻村的人,却时常会出现在她走过的山间大路上,天空闪过文蛤白的时侯,两人结伴而行,晚霞西下的时侯他又送她回去。
他带阿几听仲夏夜间的鸟鸣,摘金秋时节的枫叶,赏凛冬的红梅初雪,闻夏日的百里茶香。阿几也为他留长了毛发,开始学着梳洗装扮。只是那时侯她还不晓得,荒芜已久的心田在少年的精心滋润下总算发了芽。
阿几十八岁那年,少年考上了重点学院,并且是近六年来全村惟一一个。这是件光宗耀祖的事,隔了三个村的人都上赶着来庆祝,顺带着沾沾光。
“等我结业之后,就带你去城里生活。”
临走前,少年留下这个承诺,此后轻轻在阿几的手臂落下一吻。
他不晓得的是,皆因这个承诺,阿几捱过了五载寒冷与严冬。
原本少年都会在休假的时侯回去瞧瞧她,后来课业忙碌加之路途遥远,逢年过年也不回去了,而且每位月就会给阿几寄来一些当地特产和几本书籍。
但在少年走后没多久,阿妈便开始频繁给阿几说亲。
阿几不乐意,憋着股倔劲儿只身在山里待了一宿,逼得阿妈实在没办法了,相亲这事这才暂时罢手。眼看离少年返家的日子越来越近,连厌烦无趣的农耕生活都显得异常有趣。
——如果故事讲到这儿猝然而止,阿几会和她心爱的人终成眷属。但残酷的现实世界并没准备放过她,从来都没有。
一个女人的出现,将阿几彻底掉入万丈深渊,自此万劫不复。

时至年初,柳树吐蕊覆上了层层冰瀑,从城市里打工回去的青年相继回乡。
原本是阿几发觉有人在跟踪她,外貌和少年有些相像,以至于让她有些恍惚是不是少年回去了。不过她很快就清醒过来,那人比少年看上去要强壮,且拥有完善的全身。
女人发觉跟踪露馅之后,就常常活跃在阿几的视线范围之内,甚至还大张旗鼓地跑来她家里示好。阿爸阿妈欣慰得不行,她们只希望她赶快嫁人生子,至于将来日子能过成哪些样,那都是阿几祖上子修来的命。
“我早已有喜欢的人了,你之后还是不要再来了。”
看到这话的女人眼中犹如遍布了阴气,迫近一步:“是谁?”
阿几站在原地愣了刹那,她没想过要伤害眼前的女人,只希望对方能知难而退。她鼓起勇气,深吸了一口气,确保发出的声音依然冷静镇静:“和你没有关系。”
女人一气之下离开了,后来接连几天真的从她眼前消失不见了。阿几还以为危机解除,渐渐放下了提防心。
这天,阿几干完劳作已是黄昏时分,从果园回村里大概要走三公里的路,再越过一条繁杂的窄桥。路与桥交界处的路灯坏了,不想摸黑前行,就得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回来。
阿几刚走到桥头,就看到左侧的灌木丛里传来抖动。还没回过神来,就看到一道黑影从眼前掠过。她心中嘎吱一声,是那种女人。
女人的走路坐姿摇摇欲坠,四溢而至的酒精味呛得人头晕,眼珠由于肿胀显得通红,如同被遗忘在深山里的孤魂野鬼。阿几的心提及了喉咙眼,转身想跑,可她根本不是女人的对手,被拽回去,狠狠地摁在地上。
女人嘴巴喘着发愣,粗壮的身体下1秒压上来,手臂碾着她手臂,校服被悉数撕成碎片。
旋即,田间响起一阵异动。阿几像是捉住了救命稻草,右手右脚拚命扑腾,歇斯底里地呼喊着。头上的女人也发了狠,摁住了她的脖子,迫使她不能发声。
步伐声渐渐远逝,手掌上的枷锁才得以消失,阿几总算能大口喘息。
与此同时,天边最后一抹残阳平息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暗与静寂。
不知过了多久,刑具总算停止了,女人一手撑地爬上去,提起内裤躺下走了。
阿几仰头朝天,想要擦洗脸颊,却发觉眼泪已经干渴,黏腻在脖子上。头上混杂着腥臊的味道,让她连连恶心,她想站躺下清洗,腿却软得没有力气。
剑姬遮蔽在层层云雾里,连同她瘦小的脸庞,一同被狭小彻底映照。
她不晓得自己是如何走回村庄里的,只认为村头那桥竟这般漫长,联接果园和家的那条大路上,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阿几把自己锁死在卧室里,开始闭门不出。原本那一个月,恶梦会在夜间如期而来,那种恶魔的脸,一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她只能裹紧毛毯瑟瑟抽搐。她讨厌自己的身体,打心眼儿里认为难受,也开始轻视和任何人接触。
可惜草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命苦人,她发觉自己怀胎了。
那种女人忽然出现在家里,阿几不晓得他为何还敢来。她想拿杀猪刀狠狠劈过去,直至剁得他皮开肉绽,血水横流。
可真的见到那张遍布横肉的脸时,她就四肢颤栗,她不敢。
女人给她带来了一筐苹果和几斤香肠,无论阿几是拳打脚踢还是恶言相向,他都像只打水仗一样垂着头,悻悻地谢罪。
自此以后的每日早晨,他就会准时出现在阿几家旁边,骑着那辆简陋的四轮车陪她去果园。挖穴厨余、剪苗修枝的苦活累活,他一个人统统夺得。等到黄昏时刻,女人再跟随她回去,像块狗皮膏药似的如何甩都甩不掉。
阿几每次看到就会躲得远远的,可究竟手指拗不过肩膀,无论她干哪些活,女人就会抢鲜一步做完,在居民眼中,她的推托渐渐弄成半推半就的煽情。
她心中有过摧毁小孩的念头,可无论是村里还是镇上的医院,医疗设备根本不足以完成流产放疗。她之前据说有些婴儿病急乱投医,让人暴力揉捏自己的乳房,到最后却落得一个兄妹双亡的下场。
她开始尝试腰带束腹。可随着腹部三天三天变大,孕期的事情无论怎样都瞒不下去了。
村庄也传起了流言蜚语,有人说看到她在树丛里跟男生鬼混瞎搞,结合受孕的事传出去,哪些水性杨花、搔首弄姿,一时间都成了她的代名词。
阿爸声称要弄死她和腹部里的杂种,阿妈则日日以泪洁面,全家上下鸡犬不宁,她认为日子过得生不如死。
怀着焦躁的心情,她总算下定决心,拨打了少年的电话。
少年课业繁杂,她们已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刻,她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许久,总算拨打了。
她努了努嘴,不知从何开始说起。
要说给他听吗?虽然是全说下来,他能宽容自己经历的一切吗?
“喂?”
一道甜甜的女声,打断了她的心绪。
刹那间,阿几愕然地愣在原地。
“喂?你是谁,有哪些事——”
没等话说完,她就撂了电话。
凝望尽头,她和村里大多数女性都一样,永远只有一条命定的路。但少年的前程还有无限可能,自己又岂能和他相提并论?

后来没过多久,女人忽然上门提了亲。阿爸那如释重负的面色让她明白,自己的意见早已不重要,只要能解决眼下的窘境就行了。
那种女人于她而言是恶魔,于她家是绝望之际的救赎。
那天晚上,阿妈和她秉烛长谈了许久。
“婚姻这东西,有没有爱情不重要,渐渐培养就好了。我和你阿爸不就是这样嘛,一辈子过得也很好。”
这话说得没错。父亲出生之后,阿妈身体就落了病,早就失去了干活的能力,可阿爸却未曾想过抛弃阿妈,仍然细心照料着。
“没有女人做倚重,你将来的日子会过得很苦的。毕竟那小子将来很有希望当镇长,生下儿子,好好过日子,那一家人不会怠慢了你。”
阿几有些惶惑。她没考虑过这种,只是冥冥之中认为不对。既然自己全身完善,为何还要事事借助女人?书里告诉她,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最可靠。
“更即便你如今不是一个人了,总要给儿子安个家。”
她神色一滞,手不知不觉间伏在腹部上。那小孩像是感遭到了呼唤,肚皮微微隆起,又很快回缩。这是她第一次在自己身体里感遭到生命的律动。
究竟是由于面对少年不信任自己,而形成的报复心理抢占了上风,还是对那未出世的小孩多了些向往,她区分不明白。其实一个月后,她和女人结婚了。
社火喧天的早晨,阿几坐在女人的二八单车后排,在众人的欢送声中渐渐远离故乡。迎着爆竹声,她走到男人家门前,奶奶端来炭火搁置在她脚下。
“跨火塘,驱噩运,将来的日子才会过得好。”
阿几低头看了一眼,这炭火不大不小,正好摆在自己脚下。她一言不发地越过去,脸色没有任何起伏。
婚礼不算隆重,来的人大都是女方的舅舅好友。这些妹妹妹妹摸着阿几凸起的胸部,嬉笑着说:“肚子冒尖了,是个男娃娃。”婆婆看到这话也乐开了花。阿几拢紧头上的红袄,是个男娃娃也好,不用再经历自己所遭受的种种偏见了,她想。
阿几追随女人挨桌敬酒,却一眼见到了混在人群里的少年。他的桌上空了四五个酒壶,说话间他又续了杯酒,仰脖灌了下去。
走到面前时,少年缓缓举起头,当初那双明亮的双眼看不到了,取而代之是无尽的空洞与混沌。他晃晃荡荡站躺下来,撑着凳子勉强撑住身材,抬起手边喝了一半的酒壶,却最终摇摇耳朵,放了下去。
事已至此,她们缘份已尽,虽然不仅沉默,真的不知能够说些哪些。

阿几起初认为后半辈子也就是得过且过了,没想到那种恶魔般的女人竟对她还不错。
与女人结婚之后,阿几堪称是十指不沾阳春水。每晚夜晚,女人会做完午饭端到她的卧室,去果园干活,蒙蒙亮时回去给她做早饭,晚上又去地里除草,之后赶在五点之前回去做早饭。那一阵子,连只有春节就会登场的大鱼大肉,就会变着花样端上餐桌。
生产那日,她难产大流血,折腾了三天两宿诞下枚女童。
不晓得为何,父亲四肢长满了视网膜,毛发、嘴唇,就连眼珠都是黑色的。她的哭声尖锐清脆,听得人心惊肉跳。这让原先来看儿子的居民都退避三舍,纷纷摇头离去。
看着女人在船舷闷坐着不说话,阿几拉起他的手轻轻慰藉。
“别急,父亲的病会好的。”
女人愣了一下,突然抽出手,一语不发地走出庭院。阿几还以为他是惊吓过度,便纵容他去静静心。
不知过了多久,女人回去了,阿几嗅到了他满脸恶臭的酒气,忍不住悄声提醒。
“去洗个澡吧,别熏着小孩。”
“屁大点的女儿她能懂哪些!女兔崽子就是娇弱煽情!”
这是女人第一次冲她发火,喊声直接叫醒了酣睡的儿子,尖锐清脆的哭声再度传遍整个四合院。他骂了句粗话,愤然离去。
月子里的饭菜,女人做得越来越欺瞒,整日的饭菜都是高汤寡水,见不着一点荤菜。后来,女人又开始拿养家糊口当托词出去整日喝大酒,一回去就醉醺醺地昏倒在床上。
阿几好言好语劝了几次,女人就变本加厉,每日只备些水果和包子,往卧室里一撂就拍大腿走人。她只能下床自己做饭,忍受火光往颧骨和咽喉里钻,整日整夜咳个不停。
她听着自己腹部发出叽里咕噜的声响,每次都活生生扛过饿劲儿,实在饿极了就煮芋头青菜勉强对付几口,没几天就饿出了问题,营养跟不上,小孩吃了乳汁就开始发高烧。阿几只能抱着小孩去敲邻居家的门,恳求人家能给口盛饭。等邻居端饭过来的时侯,阿几早就倒在地上昏倒不醒,连怀里小孩的哭声都发蔫了。
等阿几挣开眼睛的时侯,她发觉自己正躺在家里的床上,脖子上埋着细针,头上挂着玻璃吊针。父亲躺在她后面安稳地睡觉,烧早已退了。
以前的少年坐在床边,曙光就照在他开阔的肩膀上。
她挣扎着想起身,反被一把按住。
“别乱跑,你如今身体还很虚弱。”少年从药箱里掏出几盒药,放在书桌上,“这些都是补充营养的,记得按量用药,早晚各一次,每次两粒。”
阿几推开他的手,将头偏向另左侧:“东西你拿回来,我的事不用你操劳。”
“就当是为了儿子。好好珍重身体。”
阿几还没说话,就听门外传来趿拉皮鞋的声音,男人身上只披了件瘦弱外衣,敞胸露怀,魁梧的脸部透着唇瓣,看样子又喝了不少酒。他其实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在这儿,面色一点点暗下去。
少年告诫了几句躺下走了,女人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砰的一声踹上了门。
阿几下意识去看儿子,见没被叫醒才松了口气。
“这上过学的就是不一样,跟他说话就是有的聊,每次我跟你讲话时就一脸不耐烦。”男人的腔调透着一股子阴阳怪气。
“有事吗?”阿几等了一会儿,没得到回复,转了个身,背对着女人回答道,“没事的话我先休息了。”
这句话如同是燃起了引线,女人突然将阿几从床上拽上去,狠狠甩了一巴掌:“是不是无论我如何做,都比不上那种跛子?”
阿几被这情形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张盛怒的脸,听着源源不断从父亲嘴巴诉说下来的污言秽语。错愕期间,她的腹部上狠狠挨了一脚,下巴撞在桌角上,胸口隐约传来疼痛的觉得。失了智的女人好可怕,密密妈妈的拳脚落出来,似乎是用巨大的石磨反复碾压她的骨骼。
阿几早没了说话的气力,在男生重拳落下的间隙,耳畔回响起母亲嘶声裂肺般的哀求声,眼前的景色越来越模糊。这一刻她很想告诉阿妈,不是每位人都能像她一样好运的,婚姻是场豪赌,而自己早已走错了路。
此后,阿几不再寄希望于父亲,为了嗷呜待哺的母亲,她开始只身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但阿几越发认为,女人对自己有着几乎病态的掌控欲,自从上一次瞧见自己与姐夫子独处之后,他无时无刻不盯住她的一举一动。原本她能够带着女儿去城市打工,后来不知如何,女人开始搅黄她的工作,在异性面前败坏她的形象,迫使她带着儿子回村。最后一次逃离村被带回去的时侯,她挨了女人怒不可遏的一顿暴打,和父亲一起被锁在屋子里过了三天一夜。
从那之后,阿几就不敢再逃了。她回到故乡,照看两家的果园,从早上到日落,回到家,继续煮饭打扫卫生洗袜子。这些怨言都藏在心底,统统化作对父亲的疼惜。
可她万万没想到,被自己捧在心尖上宠了三年的儿子,居然也会离自己而去。
她死都忘不了那三天,在半山腰的老柳树下,她发觉了父亲身首异处的遗体。遗体创口处淌出的血水还未干渴,在破旧的身体之下染成了暗蓝色的河流。
阿几看得目眦欲裂。在居民的谈论中,她得知了父亲曾带着儿子上山,却又只身一人下山,可时常问到当天发生的情形,男生却仍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
若非心中有鬼,又如何会不敢面对?
——不要放过他,要让他不得好死,要让他下地狱给儿子赎罪。

故事早已读到结尾,肖蕾沉重地叹了口气,头顶紧拧。
正值凌晨,她站在窗口过了过寒风,觉得头晕有所减轻,可心中的担忧却不减分毫。
阿几的名子不言而喻,大机率所指的正是徐凡本人。根据徐凡所写,她认为王华是谋害母亲的罪魁帮凶,那电脑旁边没拍到的内容就是她的复仇计划吗?
还有,摄像头里王阳掏出的戒指究竟是哪些,居然能让王华这么害怕?
庭院里传来踢毽落地的响声,是王阳只身在庭院里玩,她想也没想就走了出去。
“阳阳,姐姐能跟你谈谈天吗?”肖蕾笑着蹲下体,从衣服口袋拿出一根金色棒棒糖。
王阳回过头来,眼毛忽闪忽闪地眨,面露疑虑。
她将棒棒糖塞到王阳手里,轻轻掸掉女孩衣领的灰尘,语调极尽温柔。
“你去年多大了?”
王阳将整根糖囫囵搁嘴巴,吐字不清地回了一句:“八岁。”
“阿姨刚刚看见你在和谁说话,她是谁呀?”
“……”
见王阳不说话,肖蕾悻悻地接下去:“是妈妈吗?”
王阳点点头。
“你从哪些时侯开始和妈妈一起玩的呢?”
女孩没有回答,只有腮帮子里的糖果从右颊滑到左颊,因碰撞到臼齿发出刺耳的响声。
肖蕾眯起双眼,下巴的笑意却未曾削减。她缓缓站躺下来,朝他走进一步。
“姐姐陪你玩这件事,父亲晓得吗?”
啪哒一声,棒棒糖被随手丢在地上,崩裂成几瓣。
“不好吃,我不想吃了。”王阳不自然地垂下了头,目光全力避免眼神。步伐向后方搬动,看上去是想找机会走掉。
肖蕾眼疾手快地将王阳拽回原地,右手紧紧地扣住他的脖子,将小孩整个人遮蔽在自己的阴影里。她眼底的温柔一扫而空,语调顿时降至冰点,恶狠狠质问道。
“你告诉我,是不是父母让你装的,她想让你对父亲做哪些?”
“不是……”王阳身上焦躁万端,手掌倏地朝后方缩去,手指奋勇挥动,想要挣开禁锢。
肖蕾怕一脱手,儿子都会摔在地上,只好耗尽力气击溃住他。
旋即,耳畔传出一道嘶声裂肺的惊叫,几乎要穿透她的鼓膜。
与此同时,王阳的手指忽然停止了挣扎,右侧的胸肌开始持续性收缩。他的眼瞳开始不自觉上翻,漏出诡异的红色眼珠。他的颅骨朝左边偏斜,整个身体软绵绵地朝后仰起身去,足尖毫无知觉地磨擦着地面,两条手臂像大摆锤一样在空中来回晃动。
短短几秒钟时间,本来活蹦乱跳的女儿顿时弄成一个丧失意识,任由旁人摆布的提线公仔。肖蕾整个人都吓坏了,她赶快蹲下体,将女儿平躺下置于地上。
家中灯光随之亮起,两道粗重的步伐声从房间驶向正厅,紧接着冲了下来。
未完待续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信息真伪需自行辨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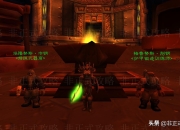




发表评论